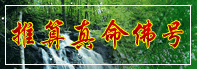中医美容,历史悠久,内容丰富,方法众多,至今仍有很大实用价值,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。早在公元一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,就有了“香汤沐浴”“月粉妆梳”的描述。
随着社会的进步,战国时期的古医方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收录了除瘕灭瘢之类的美容方。至秦汉,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,书中记载了白芷、白僵蚕、枸杞子、茯苓等几十种药物的美容作用,丰富了中医美容的内容。汉代,美容化妆品的使用更为普遍,出现了擅长化妆的专门人才和从事制作化妆品的商人。其同时代问世的《山海经》中也收录了不少增色悦泽、去疣疗痤的美容中药。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理论专著《黄帝内经》更是从经络学说、气血学说、脏腑学说等方面奠定了中医美容的理论基础,强调了要想抗老延年、延缓容貌的衰老,就必须增强五脏六腑、阴阳气血的功能,注意养生,做到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,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”。隋代,巢元方等人集体编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,对“须发脱落”“白发”“白秃”“鬼舐头”等毛发病,对“面皯”、“面疮”、“面黑”、“酒渣鼻”等颜面皮肤病,对“齿落不生“齿黄黑”“兔唇”“口臭”等唇齿病以及“黑痣”“赤疵”“狐臭”等多种影响美容的病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,初步确定了影响美容疾病的范围,在诸症之末,还附有不少“养生方导引法”,记载了气功美容和按摩美容的内容。
至晋唐时期,在中医养生防病的医学思想指导下,中医美容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出的发展和创新,使中医美容术渐趋完备。晋代医学家葛洪,在他编著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中,将中医美容的内容列为专题进行论述,介绍了“张贵妃面膏”、“白杨皮散”、“铅丹散”“令面白如玉色方”等验方,一直被后人采用。唐代,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中指出:“面脂手膏,衣香澡豆,仕人贵胜,皆是所要”,并辟有“面病”“妇人面药”“令身香”“生发黑发”等专门章节,共收载美容方百余首及彭祖导引法等可以悦泽驻颜的气功美容法。可以看出,中医美容药品及化妆品在当时地已得到普遍的运用。而且,还形成了每到腊日,君长要赏赐臣下头膏、面脂、口脂、澡豆等美容用品的习俗。诗人杜甫有《腊日》诗为证:“腊日常年暖尚遥,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凌云色还萱草,漏泄春光有柳条。纵酒欲谋良夜饮,还家初散紫宸朝。口脂面药随恩泽,翠管银罂下九霄。”唐代另一位医学家王焘在编著的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,也设有美容专卷,共分二十八类,共收方二百多首。
中医美容发展到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,在晋唐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宋代的大型方剂著作《太平圣惠方》(王怀隐等著)和《圣济总录》(宋朝太医院编)中对有效美容方剂的收集更加丰富,并补充了许多美容新方。两书共收美容方剂三百余首,对部分妨碍美容之疾病的病因和证治进行了阐述,使单纯的美容经验上升到了理论高度,使中医美容的内容更加具备了辨证论治的特色,对后世美容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。另外,宋代的美容整形术已初具规模,在南宋人所著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中就有骈指截除、缺唇修补等小儿先天畸形的整形治疗方法的记载。
元代的《御药院方》和明代的《鲁府禁方》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宫廷秘方,如“藿香散”“洗发菊花散”“孙仙少女膏”“肥皂方”等均有其实用的价值。明代朱橚等撰写的《普济方》和李时珍撰写的《本草纲目》是两部有名的著作。《普济方》被后人称为中医美容方的大汇总,不但汇集了明朝以前的大量效方,还创制了“白面方”“治酒渣鼻方”等美容新方,保存了珍贵的中医美容资料;明朝陈实功所著的《外科正宗》对许多妨碍美容的皮肤病均有系统的记载,如用“灰精”治黑斑,内服玉容散、外敷玉肌散治雀斑等,迄今仍有临床实用价值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则收录了美容中药270余种,对后世均有较高的实用价值。
到了清朝,美容用品和药剂更得以长足的发展。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法》中记载了许多皮肤美容的方法及治疗皮肤病的药物,如用水晶膏治黑闱,用颠倒散治痤疮,用时珍正容散治雀斑等等。此外,在清朝问世的《医方集解》、《张氏医通》、《外科全生集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疡医大全》等书中也散在论述了中医美容的医理和方药。在清朝宫廷中,各种美容技术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据史料记载,慈禧太后就非常讲究用美容来延缓容貌的衰老,她的美容方法算得上系列化、规范化。在清朝民间,描眉、搽胭脂、染发、香发等美容化妆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清代的整形美容术有了很大的发展,清代顾世澄在《疡医大全》记载:“整修缺唇,先将麻药涂缺唇上,以一锋刀刺唇缺处皮,即以乡花针穿丝线钉住两皮,然后擦上调血之药,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,又怕冒风打嚏,每日只吃稀粥,肌肉生满,去其丝,即合一唇矣。”从兔唇的这一修补术中足见当时的整形美容技术之水平。
随着社会的进步,战国时期的古医方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收录了除瘕灭瘢之类的美容方。至秦汉,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,书中记载了白芷、白僵蚕、枸杞子、茯苓等几十种药物的美容作用,丰富了中医美容的内容。汉代,美容化妆品的使用更为普遍,出现了擅长化妆的专门人才和从事制作化妆品的商人。其同时代问世的《山海经》中也收录了不少增色悦泽、去疣疗痤的美容中药。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理论专著《黄帝内经》更是从经络学说、气血学说、脏腑学说等方面奠定了中医美容的理论基础,强调了要想抗老延年、延缓容貌的衰老,就必须增强五脏六腑、阴阳气血的功能,注意养生,做到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,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”。隋代,巢元方等人集体编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,对“须发脱落”“白发”“白秃”“鬼舐头”等毛发病,对“面皯”、“面疮”、“面黑”、“酒渣鼻”等颜面皮肤病,对“齿落不生“齿黄黑”“兔唇”“口臭”等唇齿病以及“黑痣”“赤疵”“狐臭”等多种影响美容的病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,初步确定了影响美容疾病的范围,在诸症之末,还附有不少“养生方导引法”,记载了气功美容和按摩美容的内容。
至晋唐时期,在中医养生防病的医学思想指导下,中医美容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出的发展和创新,使中医美容术渐趋完备。晋代医学家葛洪,在他编著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中,将中医美容的内容列为专题进行论述,介绍了“张贵妃面膏”、“白杨皮散”、“铅丹散”“令面白如玉色方”等验方,一直被后人采用。唐代,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中指出:“面脂手膏,衣香澡豆,仕人贵胜,皆是所要”,并辟有“面病”“妇人面药”“令身香”“生发黑发”等专门章节,共收载美容方百余首及彭祖导引法等可以悦泽驻颜的气功美容法。可以看出,中医美容药品及化妆品在当时地已得到普遍的运用。而且,还形成了每到腊日,君长要赏赐臣下头膏、面脂、口脂、澡豆等美容用品的习俗。诗人杜甫有《腊日》诗为证:“腊日常年暖尚遥,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凌云色还萱草,漏泄春光有柳条。纵酒欲谋良夜饮,还家初散紫宸朝。口脂面药随恩泽,翠管银罂下九霄。”唐代另一位医学家王焘在编著的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,也设有美容专卷,共分二十八类,共收方二百多首。
中医美容发展到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,在晋唐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宋代的大型方剂著作《太平圣惠方》(王怀隐等著)和《圣济总录》(宋朝太医院编)中对有效美容方剂的收集更加丰富,并补充了许多美容新方。两书共收美容方剂三百余首,对部分妨碍美容之疾病的病因和证治进行了阐述,使单纯的美容经验上升到了理论高度,使中医美容的内容更加具备了辨证论治的特色,对后世美容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。另外,宋代的美容整形术已初具规模,在南宋人所著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中就有骈指截除、缺唇修补等小儿先天畸形的整形治疗方法的记载。
元代的《御药院方》和明代的《鲁府禁方》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宫廷秘方,如“藿香散”“洗发菊花散”“孙仙少女膏”“肥皂方”等均有其实用的价值。明代朱橚等撰写的《普济方》和李时珍撰写的《本草纲目》是两部有名的著作。《普济方》被后人称为中医美容方的大汇总,不但汇集了明朝以前的大量效方,还创制了“白面方”“治酒渣鼻方”等美容新方,保存了珍贵的中医美容资料;明朝陈实功所著的《外科正宗》对许多妨碍美容的皮肤病均有系统的记载,如用“灰精”治黑斑,内服玉容散、外敷玉肌散治雀斑等,迄今仍有临床实用价值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则收录了美容中药270余种,对后世均有较高的实用价值。
到了清朝,美容用品和药剂更得以长足的发展。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法》中记载了许多皮肤美容的方法及治疗皮肤病的药物,如用水晶膏治黑闱,用颠倒散治痤疮,用时珍正容散治雀斑等等。此外,在清朝问世的《医方集解》、《张氏医通》、《外科全生集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疡医大全》等书中也散在论述了中医美容的医理和方药。在清朝宫廷中,各种美容技术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据史料记载,慈禧太后就非常讲究用美容来延缓容貌的衰老,她的美容方法算得上系列化、规范化。在清朝民间,描眉、搽胭脂、染发、香发等美容化妆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清代的整形美容术有了很大的发展,清代顾世澄在《疡医大全》记载:“整修缺唇,先将麻药涂缺唇上,以一锋刀刺唇缺处皮,即以乡花针穿丝线钉住两皮,然后擦上调血之药,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,又怕冒风打嚏,每日只吃稀粥,肌肉生满,去其丝,即合一唇矣。”从兔唇的这一修补术中足见当时的整形美容技术之水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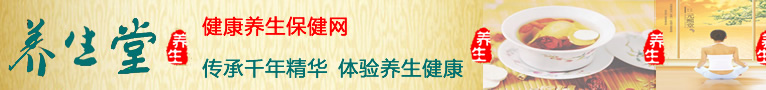
 人的运气有盛衰之别,人们在面对不可知的命数时,往往显得茫然无助。一直以来人们都有
人的运气有盛衰之别,人们在面对不可知的命数时,往往显得茫然无助。一直以来人们都有